收錄在《湘行集》內,沈從文寄給張兆和的一篇名為《第三張》的信中,有以下的記述:
“我總好像要同你說話,又永遠說不完事。在你身邊時,我明白口並不完全是說話的東西,故還有時默默的。但一離開,這隻手除了為你寫信,別的事便無論如何也做不好了。可是你呢?我還不曾得到你一個把心上挖出來的信。我猜想你寄到家中的信,也一定因為怕家中人見到,話說得不真。若當真為了這樣小心,我見到那些信也看得出你信上不說、另外要說的話。三三,想起我們那麼好,我真得輕輕的嘆息,我幸福得很,有了你,我什麼都不缺少了。”
時為一九三四年,即八十年前,一個湘西青年深深愛上一個女人,女人也愛他。文字穿越時空,昔日感人情意,活現眼前——活現在我作為一個讀者的眼前。透過文字,讓人體會在這星球上某一已過的日子,閃爍在他們生命裏的經遇。「流星掠過,帶出永恆」、「留住片刻,留住永遠」,這統統豈不是人們朝生暮死想從文字所達致的嗎?就讓我倆在這無動於愛惡的年月流逝中,佔一席位。可當我想到說話的人,已再沒有氣息,長埋地土之下,而年月再過,後人再一次為着他所觸動的觸動,對這個主體本身而言又代表什麼?對這個讀者又意味什麼?死亡就是頂絕的嘲弄者,處處揪着你的後腿,在人們悲喜中發出冷笑,在感動中展露蔑視。在那終極黑暗的光照之下,什麼也黯然無光。那一個夜,那隻山羊的叫聲,那點點的漁火,彷彿不再是溫柔,而是悲愴,是荒涼,幾近變奏成一首哀曲。
此刻除了嘀嘀嗒嗒的鐘聲,一切很靜。
《山川行》—— 絕壁上的兩條路
-
youtu.be/iCtf3j_qQUQ
新一代再沒有老一輩山民的拚勁。對於天梯,他們亦已經沒有感覺。「我一出生就甚麼都有了,現在的人一般都不會走天梯,自己有車,走它幹什麼?」
時常…
-
17 Mar 2014
荷花池
-
回中大
天微暗晦色彩濃
荷花池邊葉染紅
眾志堂外
神遊太虛故人逢
憶往昔
眼通紅
緣來緣去嘆喟中
夢醒不知去何從
-
07 Jan 2014
See all articles...
Keywords
Authorizations, license
-
Visible by: Everyone (public). -
All rights reserved
-
162 visits
Jump to top
RSS feed- Latest comments - Subscribe to the feed of comments related to this post
- ipernity © 2007-2025
- Help & Contact
|
Club news
|
About ipernity
|
History |
ipernity Club & Prices |
Guide of good conduct
Donate | Group guidelines | Privacy policy | Terms of use | Statutes | In memoria -
Facebook
Twit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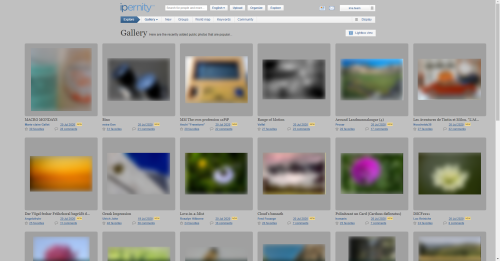
Sign-in to write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