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達香港國際機場,感受像虛無般,沒有正常出門遠行的興奮。或許是昨晚不能入睡的緣故,使得現在腦裡一片混沌,清晨的陽光不是喚醒我的感官,而是刺耀著一雙疲倦的眼睛。又或許為了這次旅程作了過度的準備,打從年初已計劃行程,多翻修改,不斷做資料搜集,心理上過多的準備消卻了正常應有的期盼,就像你做了一百次話劇採排後,到了真正演出時你已無須講求情感的自發性 ,而是為著你預知的下一個表情做準備。
從香港乘飛機前往亞美尼亞,得要到莫斯科轉機。俄羅斯空中小姐們,身穿橙色制服,但並沒有如舒拉寶娃般身材高挑、青春逼人。她們也沒有空中服務員常有的矯飾笑容,在送餐時,她們倒像 KGB 在執行任務,用俄式生硬英語堅定的問你 chicken or beef,tea or coffee,動作勤快得又像已被輸入指令的機械人般。
斷斷續續睡了好幾回,十一小時的機程也變得很快渡過;算起來中間吃過兩次午餐,一次是在上機後香港時間十二時許,另一次是在臨下機前大概兩三小時,算是莫斯科時間下午二三時。
莫斯科機塲比想像中陳舊,但也許是因為處於歐亞航程交滙區,往來班次頻繁,機塲面積很大。與我同機超過一半的乘客是和我一樣,是轉機到別處,莫斯科只是短暫逗留數小時的中途站。我要到 Terminal D,即是我要由下機處機塲候機室的一端往另一端,好不容易要花上差不多大半小時。下機時間下午五時二十分,轉機時間凌晨一時二十分,我要在這裡呆待八小時。
不知為何,一位皮膚黝黑、四五十歲的大陸同胞,手持行山用的桿,上前來主動和我攀談。一如其他陌生的旅客在異地碰面時的交談都會像指定動作般問大家兩個哲學性的問題——從哪裡來?往哪裡去?他家鄕在瀋陽,剛剛在瑞典旅行完,正在這裡等候轉機返北京。談話中間,他抱怨他的航班可能延誤,但不明為什麼航班顯示屏幕沒有交待,按印在機票的時間,理應還有三十分鐘便起飛。我問他給我看看他手上的機票,發現原來他要到 Terminal F 登機,而這裡 Terminal D 的顯示屏絕大部分並不顯示其他候機樓的班次,我指示他方向著他快趕回 Terminal F 再找出登機閘口。看見他行了幾十米外,一面行一面擧目東張西望找指示牌,很不爽快。多虧我之前下機後已走遍這機場,而且之後再行多一遍,所以我較他知道應該往的方向,於是我趕上前叫他跟我跑(正確點應是三分跑七分走)。最後我們在最後一刻成功抵疊,他感激非常,匆匆道別,雖然我們沒有(也沒必要)留下聯絡,但他叫我應到瀋陽走走,我祝他一路順風。
外出旅遊,人生路不熟,一路上總需要別人或多或少的幫助。我這㳄對同胞做出的小幫忙,在我來說只是延續之前很多人曾在我旅程給予我的幫助。我記起在泰國北碧那對兄妹、在湄宏順路邊涼亭遇見的旅館老闆、在越南順化到寧平通宵火車途中的女士。對於像我這一個天生悲觀的人,當發現身邊友善好助的人可能比想象中多的時候,總會平添一份溫暖、一絲希望,在情感上稍微體味到這世界並非如此的令人喪志。
現在登上了機,準備起飛前往亞美尼亞首都葉里溫,我坐在窗邊,窗外下著細雨,漆黑一片中閃照著零星的燈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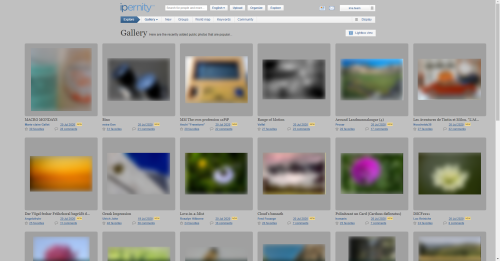
Sign-in to write a comment.